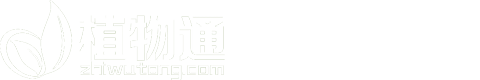寻找蓝罂粟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作者:孙 敏 日期:2008-03-01
生长在中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高原植物绿绒蒿,自18世纪以来,就受到西方植物学家关注并采集。这美丽的花卉,不仅在世界上拥有炫目的观赏价值,也在中国藏族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还是藏药中不可缺少的药材。在西方,她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蓝罂粟”。
在川滇交界处的大雪山上

黑沉沉的云雾从云南方向弥漫过来,掠过幽蓝的冷杉林,一路朝着川滇交界处的大雪山涌来。山峦的最高处是一列因寒冻风化剥离得只剩嶙峋峰刃的石灰岩山体,锯齿状的轮廓在流动的大雾中渲染着诡异和神秘。石灰岩山体下大片的流石滩毫无生气,光秃秃如月球一般荒凉。
流石滩的下方海拔4500米,就像生命的分水岭,植物正从贫脊的土壤中萌发,在东喜马拉雅的莽野里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力量。那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五花草甸,深浅不一的粉色蓼科植物覆盖在山坡上,像一层柔软的地毯。花形千差万别的马先蒿开着紫色和红色的小花,像镶嵌在地毯上的图案;龙胆从绿色草甸上发出幽蓝的微光,草丛中的翠雀像飞舞的小鸟。还有报春、金莲花和灌木状的攀援铁线莲,五彩斑斓的高山花卉在短暂的夏日展现着它们令人惊讶的生命力。山坡另一侧是一大片被山火烧过的高山柏,枯死的躯干虬蛇般蜷伏在地表,枯枝丛中,一簇簇黄色的花朵在冷风中摇曳着轻薄如纸的花瓣。这些高贵而美丽的花朵就是辽阔的喜马拉雅群山中的传奇绿绒蒿。
Saul Cunningham博士在观察传粉昆虫的活动,他要确定这种绿绒蒿是虫媒花还是风媒花。在一朵开花的植株上,很多小蝇坐在花瓣上,偶尔来回爬动,却不去访问布满花粉的柱头。在那一天的笔记里他写道:“花内监测温度10摄氏度,空气中的温度可能只有9.5或者9度。对昆虫来说,也许10摄氏度是一个限制温度。我没有看到食蚜蝇有传粉活动,也没有在绿绒蒿的花中看到任何蜂类,我猜测这个实验点之所以缺少传粉昆虫,大概是因为气温太低的缘故。”
谢鸿妍在为这些美丽的黄色花朵做体征测量:每一棵植株的大小、每一片叶子的长度,以及花苞和果实的数量。她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研究中国藏东南地区绿绒蒿属植物的保护生物学。她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学院植物和动物系的植物学家Julian Ash博士、Adrienne Nitotra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的昆虫学家Saul Cunningham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对绿绒蒿属植物进行种群生态学研究。

2006年夏季以来,他们从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到川西北的甘孜、阿坝,以及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和海南,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广阔地区建立实验点,监测了若干种群,以期对绿绒蒿属的生命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目前这一物种面临着采集过度和生境破坏的威胁,研究它们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种群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变化,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保护繁育模型和可持续的管理手段。
大雾到来之前,冰冷的风已先期袭来,又要下雨了。2007年入夏以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似乎从未间断过向横断山脉带来雨水,云南西北部和川西北持续低温。刚开始的实验很不顺利,整个6月里,研究小组从云南到四川到青海,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部来回奔波数千公里,结果却令人气馁:今年物候反常,需要监测的群落没有按花期开花,上一年做过的原生境种子发芽试验颗粒无收。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环境里,高山植物的保护学研究来得尤其艰难。持续的全球暖化,物候反常,再加上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都对高原生境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2007年11月的这次,是当年夏季实验的最后一次出野外,比对2006年以来的记录,研究小组借此了解植株在一年里的生长量和它的营养分配过程,它们以多少生长量用来繁殖生长?又以多少生长量用来营养生长?高寒环境里,植物可能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积蓄能量,才能最大量地产生花朵延续它们的后代。
喜马拉雅罂粟的诱惑
云雾托不住水滴的重量,终于变成冷雨铺天盖地的横扫过来,吞没了四周的雪峰和峡谷,让一切变得混沌。天色已晚,穿越川滇边界的道路曲折而泥泞。公路的一边是深深的狭长山谷,在灰暗的暮色里让人望而生畏,谷底的激流像一条白色哈达,落差使它一路撞击着砾石被摔成雪白的泡沫,隔着二十多公里都能听到它的咆哮;另一边是大山,悬在山崖上的只是一条简易公路,汽车得小心滑行。四周是如此的宁静,除了划过空中的鸟鸣,就只有我们汽车的发动机在群山间孤独地喘息。
透过雨幕,不时能见到报春、鸢尾、乌头、翠雀和成片的杜鹃。在植物志上,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高山花卉。100多年来,无数的生物学家都梦想着进入这个自然殿堂,在地球最高的高原上,领略这个植物世界的丰富和非凡。
一个多世纪前的喜马拉雅东部地带还是一个陌生世界,是那个时代不怕死的法国传教士,最早向西方园艺界描述了这个花卉的天堂。19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教皇将中国藏区划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布道区之后,就有不少法国传教士活跃在打箭炉、巴塘、芒康、大理、中甸一带。上帝的使者们在这片荒原上发现了一个植物新大陆,于是传播福音之余,植物采集成了他们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有最早发现鸽子树的大卫、在川西打箭炉采集的苏利埃、川东大巴山采集的法尔热、在巴塘传教的蒙贝格,以及负责云南教区的代理主教麦尔和迪克洛等等,他们都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欧洲的各植物研究机构送回过无数的植物标本和种子。这些人当中声名最显赫的就是赖神父(1838—1895),他在云南的大理和丽江一带采集,13年间就送回巴黎自然博物馆20万号约4000个种包括1500个新种的植物标本,以及数百种来自云南的植物种子。

传教士们只是打开了宝库的一扇窗户,真正开启大门的是随后到来的专业植物猎人。物种引进在西方有着久远的传统,植物移植被看作是一种伟大而独特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无数探险家遍及全球的探险活动点燃了世人对异域植物的激情,种植新发现的植物成了欧洲花园的时尚。植物搜集被视为推动人类理解自然界的重要动力,植物猎人们从北美洲、非洲和中东带来的新奇植物,装点着欧洲的美丽园林。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皇家植物园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等机构,纷纷资助和派遣受过良好教育的植物学家到偏远的未开发的地区搜集新植物,花卉企业如英国著名的维奇公司也热衷于资助自己的植物猎人。这些勇敢的植物猎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遥远的东方带回了数量惊人的新植物,深刻地影响着欧洲植物和园艺界的研究与发展。就如欧内斯特·威尔逊写到的:“在整个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不栽培数种源于中国的植物。”
从法国传教士们“顺便”从中国西部带回来的标本中,英国最古老的私营花卉企业维奇帝国的负责人敏感的哈里·维奇爵士嗅出了其中的诱惑中国西部存在着极其丰富的植物群。他决定派一位采集者到中国去,这位采集者就是23岁的年轻人欧内斯特·威尔逊。1899年威尔逊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他找到了法国传教士大卫1862年在川西发现的鸽子树珙桐,同时带回了大量的观赏植物。1903年威尔逊第二次来到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绿绒蒿。
绿绒蒿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更为人所知,那就是蓝罂粟。因为这个属里有几个种的花是呈稀有的蓝色,那是在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的高原上才会有的颜色。

学界对绿绒蒿属植物的研究约有200年的历史。它最早的名字叫欧洲罂粟,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根据生长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绿绒蒿命名的。植物分类学博士李嵘告诉我,林奈1753年在《植物种志》上首次描述这个种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了罂粟属的植物。绿绒蒿与罂粟同属一个科,它们都是很原始的一类种子植物,进化程度不高,进化方式也不多。直到1814年法国植物学家Viguier研究该种植物时,发现绿绒蒿属植物的柱头不同于罂粟属,它有一个短短的柄从子房处伸出,于是将绿绒蒿从罂粟属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新属。
- 闁靛棗锕g花顖炲础濡や緡妲婚悶姘煎亐閳ь剚姊婚弫鎾诲箑娴i鐟㈤柣銏㈠枔婢у潡宕烽幍顔藉€為悷娆欑秬椤曚即濡寸€n亜姣夐柣妤€鐗炵槐婵堜沪閺囩姴绠涙俊鐐茬Х椤箓鎮崇€n亝绂囧鍕噹婵拷 [03-15]
- 婵炲柌鍕哎濞戞挻绮屽畷锟犳焾閵娿儱绲洪柣婊勬緲閺€顏囥亹閵忋埄娼犻柡鍌涙緲閻﹢鍨鹃弬琛″亾閺傚灝宕ラ梺鎻掓唉婵牗銈圭拠鑼剑 [03-15]
- 闁烩晝鍋撻悡鎾嫉閵娿儱顕ч柣顓℃珪瑜邦喚绮堥悜妯肩煆闁告顨呭﹢鎾礌閻戞ɑ绂堥柟鏋劜濠€渚€寮撮弶鎴犵暛閻炴哎鍊楀▓鎴︽倻椤撶偟鏁ㄦ俊鐐茬Х椤拷 [03-15]
- 婵$偛绉舵晶鍧楀礌閺嶎偆鍙鹃柟娲诲幘閵囨碍绋夊⿰鈧花鍦暜閸濄儴闆归梻鍐╂煥瑜伴箖寮稿Δ鍕闯婵犙勫姉濞堟垿寮崜浣叉晞鐎殿喖鍊藉婵嬪箑閿燂拷 [03-15]
- 闁哄绀侀惃顒傜矓瀹ュ洤鍙冮梺鎻掓捣閺佹挸顪冨鍥р挅濡炶鍓欓崣褔骞庨妷锔叫氶柛锔哄妽濡插懘寮版惔銏╂Щ闁绘せ鏅涘ú顖涳純閺嶎煈鍋х€殿喒鍋撻柤鐚存嫹 [03-15]
- 闂傚牊甯熷Λ灞绢殗濡搫鏂ч柛锔藉閵嗗倿宕樺鍡楁綉闁哄倹婢橀惈锟� [03-15]
- 闂傚牊甯熷Λ灞绢殗濡搫鏂ч柛娆愬灩楠炲洦绋夐妶鍥舵綒闁告帗妞介幗閬嶆嚀閾忣偅鐓€闁绘せ鏅濋~锟� [03-15]
- 閻犲鍨哄Λ妤呭炊閵忋倖袝闁告瑦鍨电粩閿嬵殗濡壈鍓搁柍銉︾矎缁夊鐥娴兼劙宕楀畡鏉跨樁闁炽儲绻愮槐婵嬪礉閳轰礁顫旈柛鈺勬椤㈠懘鎯嶉弮鍌楁晙闁告粌鐭傛禒鎰閻樺搫浠滅紒澶涙嫹 [03-15]